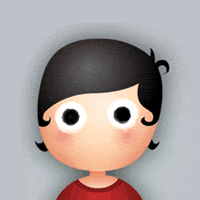|
A
远处三只棕熊吸引了查利
·
拉塞尔的目光。当它们离他一米左右时,这些巨大的动物就会放慢速度。领头的熊把脸紧紧地贴在拉塞尔的脸上,她用自己的鼻子碰了碰他的鼻子,拉塞尔突然笑了起来,
"
嘿,小熊,
"
他说。
现年
70
岁的拉塞尔在俄罗斯最东部的地区与棕熊一起度过了
10
多个春夏。
"
毫无疑问,熊是危险的,
"
拉塞尔说,但他也认为,害怕它们会阻止我们认识到它们聪明、顽皮、和平的本性。
"
他们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虐待他们。
"
他强调。
"
我现在想做的是在这个问题的人性方面进行研究,
"
拉塞尔说。在加拿大,城市延深到乡村地区,猎人每年捕杀大约
450
头熊,他决心改变我们对待我们(熊)邻居的方式。
拉塞尔从小就被灌输
"
只有死熊才是好熊
"
的观念。他的父亲是一名猎人,会和五个孩子分享残忍的棕熊的故事。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家族狩猎事业衰落,拉塞尔加入了父亲的探险队,去阿拉斯加拍摄棕熊。拉塞尔不禁好奇,为什么熊会对携带枪支的人表现出攻击性,而不去攻击电影制片人。
"
我猜测他们不喜欢残忍,
"
他说。
1994
年,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库西姆阿丁灰熊保护区峡湾验证了他的理论,在那里,他带着游客进行观熊之旅。一天下午,在导游间隙,拉塞尔坐在一根圆木上休息,这时,一只母棕熊不经意地走近了他。
"
我知道如果我不动,她会继续(向我这里)来,
"
他后来说。
"
我决定让她想走多近就走多近。
"
拉塞尔语气轻柔地和熊说着话,熊就坐在他的身旁。她把爪子放在他的手上,拉塞尔回应了她的手势,摸了摸她的鼻子、嘴唇和牙齿。这些曾是父亲在篝火旁讲的故事里的(熊的)
"
铁颚
"
,现在竟和一只小狗的鼻子一样没有威胁性。如果他能重复(经历)类似的事情,拉塞尔相信他能证明
"
只要善待熊,人们就能安全地与它们生活在一起
"
。
B
一项对
1 000
人的调查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60%
的员工每天都在办公桌前吃饭,而三分之二的员工只花
30
分钟或更少的时间吃午餐。这意味着他们每年要多工作
128
个小时
——
相当于每天
16
个
8
小时工作日。即使员工真的离开办公桌,他们通常也在工作,近四分之一的人承认自己经常利用这段时间与专业人士保持联系。
职场科学的一位学术专家表示,员工拒绝午休,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冒险。阿斯顿大学商业合作副院长
Tissington
博士说,人们在工作中感到
"
有压力
"
,很多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
"
敲击着键盘,盯着屏幕,以不好的姿势坐在不舒服的位置上
"
。
他说,对工作者来说,有规律地休息、起来和走动是很重要的。他说
:"
在中午休息一下,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绪,为高效的下午做好准备。
" "
因午休而产生的负罪感是一个令我担忧的话题,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查,
"
他补充到。
Tissington
博士提到,他在午餐时间一定要离开办公桌,故意选择从不同的地方吃午餐
——
选择不同的路线去那里。他解释说
:"
这会带来锻炼的额外好处,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它让我有机会在路上结识不同的同事。
"
办公室职员们承认,为了发展事业,他们牺牲了午休时间。
24
岁的公关助理
Tammy Phillips
说,过去两年他都没有午息过。他说:
"
我的看法是,当午餐时间比较安静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工作,而且当你的同事们出去吃三明治的时候,老板们看到你坐在办公桌前,对你的职业生涯不会有坏处。
"
"
现在找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戒烟是因为不想让人看到他们白天出去抽烟。
"
C
"你是哪里人?"他们问。"猜猜,"我说。有人说我有日本人的眼睛,其他人认为我是菲律宾人,也许是印度人。极少有人能猜中事实:我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但我并不是唯一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我是年轻一代美国人中的一员,我们的身份既不取决于我们来自哪里,也不取决于我们最终在哪里。
我父母对加州移民的经历了如指掌。他们在
圣华金山谷
摘水果长大,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但也知道身为墨西哥人意味着什么。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上了大学,找到了专业的工作。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了中产阶级。我在萨克拉门托种族混杂的地区长大,当我的父母谈到他们在田间的岁月时,(我)很难把这些故事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联系起来。
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差异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都在为自己的个性而奋斗,四处寻找,却看不到自己来自哪里。身份变成了商品,社会阶层由穿某种衣服,喜欢某种音乐划分。
我变成了一个拾荒者,在过往的流行文化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碎片。当我爱上了披头士乐队时,我把自己和英国联系在一起。当我被日本漫画迷住时,我就上了语言课。
我的成长过程过度的美国化,几乎没有考虑过我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人性。我离开萨克拉门托,搬到旧金山寻找自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族人生活在独立的社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我从未学过的语言。看着我棕色的脸,人们用西班牙语向我问路,我只能以大家都能理解的耸肩来回应(他们)。
"这就是我,"我看着满是新移民的街道自言自语道。不,不完全是这样,我纠正自己说:"我就是来自这个地方。"
我在远离母国文化的地方长大,并在这么晚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这是一场悲剧吗
?
我更愿意相信,我的美国式教养教会了我如何将自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我不仅仅是墨西哥或美国的产儿,而是整个世界的产儿。
|